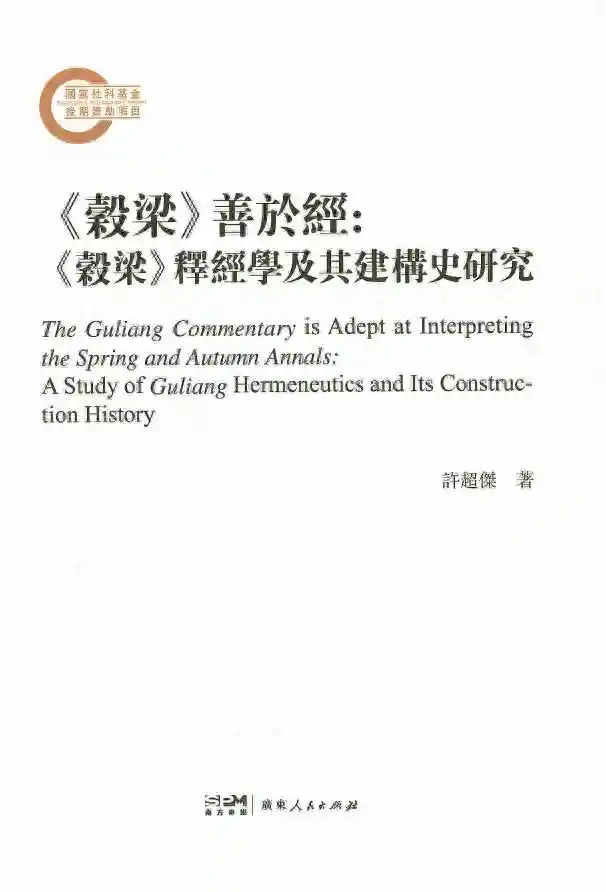
《穀梁》善於經:《穀梁》釋經學及其建構史研究
許超傑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24年10月
內容簡介
本書是對西漢以降歷代《穀梁》釋經學史及《穀梁》學體系的學術史研究。分為上下二編。上編以“《穀梁》釋經學及其詮釋體系研究”為主題,以“《穀梁》善於經”為核心脈絡,以西漢以降儒者尤其是歷代《穀梁》家對《穀梁》釋經體系及其價值的研究為對象,對《穀梁》詮釋學史予以探討,主要以鄭玄、范甯、楊士勛、阮元、許桂林、柳興恩、鍾文烝、柯劭忞等詮釋《穀梁》學者為中心。下編為“《穀梁》釋經新詮”,即以柯劭忞所建構的《穀梁》學體系為中心,以“九旨”與“三臨之言”為核心標准,對《穀梁傳》傳文予以專題新詮。主要包括對“元年春王正月”“西狩獲麟”“齊桓晉文之事”的再詮釋。
許超傑,浙江慈溪人,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經學與經學史、《春秋》學、文獻學。
目錄
序一守先待後紛陳其新(戴揚本)
序二《穀梁》學史開新篇(李紀祥)
緒論1
上編《穀梁》詮釋學史與詮釋體系研究
第一章盛衰繼之辯訥:漢代《穀梁》學説略13
第一節廢興由於好惡:“宣帝善《穀梁》说”發微13
第二節鄭玄《春秋》學發微:以“《穀梁》善於經”之詮釋爲中心47
第二章集解與義疏:《穀梁注疏》釋經模式研究75
第一節集解《穀梁》:范甯之《穀梁》學與《春秋》學76
第二節義疏與正義:唐初義疏學視域下楊士勛《穀梁疏》95
第三章再发现與新詮釋:“《穀梁》善於經”視域中的晚清《穀梁》學
第一節傳承與共構:阮元與晚清《穀梁》學的再發现111
第二節重構《穀梁》時月日例:許桂林《榖梁釋例》研究128
第三節治諸侯與日月例:《穀梁大義述》與“《榖梁》學”體系之建構151
第四節《穀梁》最善於經:鍾文烝《穀梁補注》約論166
第四章九旨説與三臨言:柯劭忞之《穀梁》學體系建構182
下編《穀梁》釋經新詮
第一章敘事與賦義:《春秋》三傳釋經體系異同論217
第二章正隱以治隱:《穀梁》體系中的隱公敘事246
第三章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穀梁》“西狩獲麟”義解261
附錄文本詮釋與現實投射:杜預、范甯《春秋序》中的歷史與建構272
參考文獻292
後記302
守先待後紛陳其新:戴揚本教授序
許超傑博士的新著《〈穀梁〉釋經學及其建構史研究》,是他近年来所事清代經學史研究工作的總結之作,即將付梓出版,誠為可喜可賀之事,然超傑的作序之命,却令我內中惶恐。治經學之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前人已多有慨叹,说起来,一部《十三經注疏》置於案頭多年,於我不過是讀書時供檢索之用的工具書,所以一時間我腦中竟有“何敢贊一言”的念頭,躊躇良久而未得下筆。雖然,超傑的新著,發端於六年前的學位論文,是他在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讀書研究的階段成果,作為古典文獻學專業的導師,常與他一起討論課題,並分享各自讀書治學的心得,十年前的情景,宛如昨昔,已經成為我們共有的親切回憶,作為早先的讀者之一,似有當然的責任,故勉力寫上幾句自己的認識和感想。
《春秋》三傳,各有所長,《公羊》和《左傳》兩家,藉漢代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興盛,乘勢而起,在兩漢數百年間各領一段風騷,並成為影響深遠的顯學。惟《穀梁》之學,雖有漢宣帝在“石渠會議”上為之設立太學博士,畢竟是一時之力,此後范甯為《穀梁》作注,“辭辯而義精”,終未能挽回大勢,《穀梁》之學竟在之後的千餘年時間裡落寞而至式微,專著寥寥。及至千年之後的清代中期,宗鄭之風使得乾嘉學人以鄭玄“《穀樑》善於經”之說為研究的再出發,千年沉寂後,如忽聞空谷足音,《穀梁釋例》《穀梁禮證》《穀梁大義疏》和《春秋穀梁經傳補注》等一系列著述的問世,渙然而為經學史上的一段復興新流。
超傑的新著,雖說發端於學位論文,卻也是一次個人研究的再出發。通覽全書,早先的論文是以“《穀梁》善於經”為主線而展開,將清代學者許桂林等《穀梁釋例》等四種著作為研究案例,分析工作貫穿清代的《穀梁》學發展的脈絡,不乏新見。而今天的新著,經過數年時間的從容修改,不僅補充了大量新的文獻資料材料,更有對《穀梁》學史的源流及相關史事新的梳理,全書面貌煥然一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討論中結合近年來研讀闡釋學理論的心得,對《穀梁》學史相關問題提出了許多新的看法。這種置於宏大的歷史背景下剖析披究思想脈絡方法,結合他原本就文獻爬梳整理的细密工夫,他的一些見解顯然有別於我們常見說的“經學史”式的著述,這應該是他將書名賦以“建構史研究”的涵義所在了。
有別於傳統經學的研究路徑,本書研究開展的方式便具有一種別開生面的特色。如對於所謂《春秋》學熱點的取向,溯源自漢武帝親自策問以古今治道;敘漢宣帝崇《穀梁》之學,則以疏廣見微知著的退身之舉為發軔。在相關的文獻中深耕細作,極盡披沙揀金之功。對學術史上的一些定論,亦多能不株守成說,引證豐富的史料後提出自己的看法。鄭玄作爲漢末大儒,遍注群經,是中國經學史上最重要的儒者之一。歷代對鄭康成多所推崇,原因是當時流行的儒家經典中,《禮記》《周禮》《儀禮》《詩經》皆採用的是鄭康成注,故而“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至明代,隨著程朱理學取代漢唐注疏,鄭玄地位一度下降,而從清前期開始,考據實證之學漸成學界主流,隨著考據學的勃興,鄭玄又成爲第一位階的儒者。從表面上看,隨著清中前期開始鄭玄地位的上升,特别是《穀梁》家的重新發現、再解讀,“《穀梁》善於經”被轉換成《穀梁》較《左傳》《公羊》更善於經,所謂《穀梁》解經才是《春秋》真義,促進了清代《穀梁》學的興起,是貫穿清代《穀梁》學發展的脈絡所在。然作者以為如此解讀,不止失之簡單,甚至是清代《穀梁》家有意無意的誤讀。至於對在《穀梁》學史上曾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學者的思想,如被喻為杜預“美好期待”的“聖人制作”,抑或范甯在《穀梁》注文中流露的無望悲歎,杜預、范甯之不同,與其說是二傳家法之不同,或者說文本解讀之歧異,毋寧說是歷史投射之差異。歷史的後見之明已經告訴杜預,也告訴范甯,更在指示我們,平王東遷意味走向衰落,而沒有能夠“紹開中興”。作者帶有濃郁的歷史色彩的歎息,很自然地令我們聯想到闡釋學的一個觀點,即所謂的傳統,其實並非我們繼承得來的一種先決條件,而是我們的認知和我們的思想“指導”它產生出來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规定了传统。這類以“歷史投射”來解釋何以理解“傳統”的內涵,不止一次出現在行文中,對於傳統思想演變的思考,包括對經學史上出現的紛爭的理解,無疑有很大的啟益。
超傑的治學路徑始於史學,而後由文獻學的專業訓練再進入學術思想史的研究,故而在研究中表現出來的“歷史感”,似乎是有著順理成章的順序。然此次讀了他的新著,我感覺到這種強調歷史感的意識,與其說來自史學訓練的基礎,不如說更顯示的是他近年來讀書治學所獲得的闡釋學的啟益。所謂“歷史感”,不止是歷史背景知識的敘述,更重要的是一種自覺的思維方式,就像研究社會須從最初的社會經濟關係出發一樣,研究思想應該是研究感性活動的主體即人的種種社會活動入手。看似不甚相關的歷史活動,沉潛其中,就會感覺到史事背後隱含著的互相牽連的線索。通過對歷史上諸多論爭的梳理,提示我們在研究文獻的時候,對於文本的理解,僅從字面上的解釋是膚淺的,須就這些歷史活動線索悉心辨析和梳理,並立足於自己內心的體驗,努力建構當時作者的內心世界,如此才可能實現解釋者和作者的心靈溝通。超傑在新著中由政治與學術之間的關係切入,嘗試從歷史事實的考證入手,尋繹其間的邏輯關係,正是這種運用“歷史感”的努力表現。
清代學者戴震曾引述友人之言,深歎“學者莫病於株守舊聞而不復能造新意,莫病於好立異說,不深求之語言之間以致其精微之所存”。治學未能求創新之意,而以立異說自相標榜,其實是學界一種根深蒂固的通病。所謂“治經所以干祿”,雖是歷史上的儒生故事,因有利益相關的緣故,回環四周,還是可以感覺到這種若即若離的陰影的存在。超傑治學,志存高遠,能文章而善考覈,更以“志乎聞道”為追求之的。作為世紀之交成長起來的一代學人,他們擁有許多優越的條件,一個顯著的特點便是思維活躍而學術視野開闊。以超傑個人言,藏書極富,又擅長利用網路數據庫資源,敏銳地關注前沿動態,卻從不以文獻堆砌式的引證作內涵乏乏的所謂學術探究,不屑以之炫耀所謂的引證弘富和學識淵博,也不盲目追趕所谓的热点和時新的“課題”。幾年來,作為一個旁觀者,無論是讀他的新刊論文抑或新著,都能感覺到他在努力把握自己的追求方向,通過開掘點點滴滴的細節,提出自己的新見解。超傑治學的早些年曾有幸得到時永樂先生的悉心栽培,奠定了文獻學的厚實基礎,在他後來的學術發展歷程中,轉益多師,得到虞萬里先生和李紀祥先生的教誨,這是超傑尤為幸運之事,兩位先生在經學方面積蘊豐厚,超傑的經學文獻研究能有較高的起點,受諸啟益而多有收穫,無疑是與之密切相關的。超傑為人誠慤,專心向學,近年來對四庫學的研究孜孜不倦,仍然是在文獻領域進行深耕的功夫,嘗試進行學術思想史領域的系統探究。翻覽新著,我讀到了書中引用的錢賓四先生之言,“中國儒學最大精神,正因其在衰亂之世而能守先待後,以開創下一時代,而顯現其大用。此乃中國文化與中國儒學之特殊偉大處,我們應鄭重認取”,我以為這也是超傑所追求的治學旨趣。牟宗三先生曾經說過,在知識世界的背後,有一個與學習者的生命品質相關聯的價值世界,而價值世界的建立,又與知識世界的充分展開密不可分,無論為人或為學,同是要拿出我們真實生命才能夠有真實的結果。在我看来,超傑近年來的努力,亦正是在用自己的人生踐行他的生命品質相關的價值世界,未知超傑老弟以為然否?讀了他的新著,不禁遥望南天,更增加了對他未來研究成果的期待。
《穀梁》學史開新篇:李紀祥教授序
許博士超傑君大作《〈穀梁〉善於經:〈穀梁〉釋經學及其建構史研究》即將問世,問序於余,余與許博士相交逾十餘載,於學問性情皆相契,且序者緣情起意,述義道學,雖學不逮,有不容辭者。
許博士之大作蓋專門之學也,其書分上、下編,上編《穀梁詮釋學史與詮釋體系》,凡四章;下編《穀梁釋經新銓》,凡三章;全書共七章,若計緒論、附錄,則凡九篇。近世以來,治《左氏》與《公羊》者多,治《穀梁》者絕少,許君此書之問世,正可為海內《春秋》學界增添一采。若然,則是書所以述、作者,不可不定其學史位階。
一部《春秋》長河千年,《穀梁》獨稱絕學,因學絕而絕學,固已道盡《穀梁》學難治辛苦矣。前賢雖有東晉名家范甯集解全本之注,後又有楊士勛疏,今皆並傳;然較於《公》、《左》二家,其實頗為中落。至清代漢學興,《穀梁春秋》亦在其中,遂有許桂林、柳興恩、鍾文烝、柯邵忞等,對范甯《集解》頗微詞,故清儒《穀梁》解《春秋》皆欲另闢路徑,與六朝背景殊緻。范甯於南方著《集解》,以為漢世先師多採二傳,不能專宗《穀梁》,自成體系,亦不能使“《穀梁》善於經”;然范甯又自名其書“集解”,雖曰集講共讀之長,實則深採《左氏》與杜預,甚或《公羊》說,又有自違者。
昔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載孔子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自衛反魯後,則“雅頌各得其所”;又載“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故後世學者多錄焉”。未言夫子身後傳學系譜。《史記》述“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闕焉”,故司馬遷所載皆自漢傳而錄,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趙自董仲舒;《儒林》則記稱董仲舒“以治《春秋》”,又云“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傳則記“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儒林》雖有瑕丘江生小傳,稱其“為《穀梁春秋》”,為漢初傳《穀梁》之始,然其學不顯,須逮宣帝時,《穀梁》始興立。故本書言《穀梁》學史首章,即自宣帝朝始,蓋探欲其學顯之要。據司馬遷所載,知公孫弘以儒興,顯達後復議請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貌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員,得“受業如弟子”。堪注意者,司馬遷所述漢傳《春秋》敘事,此時並無《左氏》傳《春秋》之言說。則迄於漢武,《史記》中所載漢傳《春秋》之述,實僅二家而已。傳《公羊》者顯,立於學官,史公皆稱其為“授《春秋》”“治《春秋》”;而江生傳僅稱“為《穀梁春秋》”;則漢代前期兩傳之顯晦消息,已在司馬遷筆下歷史成形。若《穀梁春秋》之成顯學,立於漢廷學官,其事已在司馬遷後,而進入《漢書》世界。
宣帝為武帝時衛太子後,親臨石渠之會,從而促成《穀梁》學興,蓋此實關涉《穀梁》何以興立。許君自石渠閣會議切入,提出《穀梁》釋《春秋》經文末字“麟”與漢家政權關係,確是一個特殊角度,彼並未追隨為漢制法的開國性立言,或是具有變化性的“漢制”指向。依許君所云,石渠會後,《穀梁》作爲《公羊》挑戰者,係被宣帝推上歷史政治舞台;故石渠會議所反映者,正係以漢宣為核心而展開的《春秋》學政治。石渠會後黃龍元年宣帝設立十二博士,《穀梁》正式成爲博士官學。毫無疑問,因宣帝之推動,《穀梁》獲得前所未有之重視與地位;一如《公羊》,因武帝崇儒策問,方有《公羊春秋》之大顯。廟堂與學術間,誠有深切可言者。
班固《漢書·藝文志》載“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又曰“《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其所記載較諸《史記》已有增詳,云《春秋》之傳增為五家,唯存三家,此《春秋》左氏、公羊、穀梁並稱三傳之起。《藝文志》又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可知除《左氏傳》三十卷外,其餘四家之傳本皆為十一卷,此即經文莊公、閔公合為一卷,為《漢》史言經十一、十二卷張本。依《藝文志》所述,則可見司馬遷未曾言之三傳並立,已在《藝文志》中並稱。蓋《藝文志》所述孔子後《春秋》傳衍,讀之則貌似三傳自古即並存,同解孔子之經,故稱“三傳五家”;然實非如此。班書載“《左氏傳》三十卷”,知班固當時的《左氏傳》文本,已然面向解經化而“章句化”,方有三十卷之言,蓋解《春秋》為經而章句也。班固所處時代已在東漢,其所見記《左氏傳》傳經背景,實源自劉歆。《漢書·楚元王傳》載宣帝時詔劉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又載成帝時劉歆受詔“與父劉向領校秘書,云:
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
此即《左氏傳》面向解《春秋經》章句化之背景。此前《左氏傳》實為單傳,未以解經而稱傳,故傳習者但訓詁其古文古字而已,其篇卷之數則文獻未載;至成帝徵書政策興,劉向、歆父子相繼典校書。劉歆因大好《左氏》,有倡議《左氏》傳《春秋》之論,此事則在哀帝時,故“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遂作書《讓太常博士》,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謂太常學博士以為《左氏》不傳《春秋》經,“豈不哀哉!”故此時學術主流仍不以《左氏》為傳《春秋》之傳,劉歆所以得罪名儒,復遭大司空師丹問罪,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故歆既“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遂遭貶外;直至歆、莽再起,方於王莽主政下,《左氏》得立學官。故歆所以爭立《左氏》,亦與其解經並進行章句化有關,此哀帝所謂“歆欲廣道術”也。班固《藝文志》所載,本有古文立場,故其所錄“《左氏傳》三十卷”,正可反映班氏對劉歆《左氏傳》解經化行為之支持態度;若西晉杜預之《集解》者,推進劉歆以來《左氏傳》章句化趨勢,終至編年比次,“集解”以為經傳合本章句化之終,即今本之貌,亦可在此脈絡下理解。
如是,由劉歆至班固是一層經學史背景,此時《漢書》已錄傳《春秋》者為“三傳並立”;而自班固迄漢季鄭玄,又是另一層經學史背景,東漢《春秋》今學與古學並競,鄭玄此時言說三傳特色之比較:“《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許君於書中命名鄭玄此三傳較論為“三善說”。三善說中“《穀梁》善於經”者,即許君所以命名其書之意,其緒論言課題開篇發端,與所以旨趣之軸,皆在於是。吾人若取劉歆《讓太常博士》與鄭玄“三善說”相較,則可發現一種攸關《左氏傳》的歷史變化,正在此二事件座標時間中顯示。劉歆移書太常諸博士,太常博士亦讓劉歆,而太常觀點是朝廷主流認知,並不認可《左氏》之傳《春秋》,亦適反映官方主流實未有《左氏》傳經之論;此移書不僅反映劉歆所倡為新觀新說,亦可證哀帝時漢傳《春秋》僅有“二”傳。則由“二傳”至於“三傳”,鄭玄之三善說,其實正與何休之《三闕》相同,皆已充分說明漢季經學史變化與態勢:《左氏》進入“《春秋》學史”範疇,“三傳”並列,並被鄭玄提出比較。知此,方可考察東晉時的范甯《春秋穀梁傳集解》之經學背景,范甯面對的《春秋》學史,已不再止於漢哀帝前的《公》《穀》之爭,而毋寧更是三傳間的競合;蓋范甯作注兼採二傳,尤親鄭玄、杜預,必《左氏》已同屬《春秋》學範疇方可。
本書上編第二章便係許君專門討論范甯《集解》并楊士勛《疏》之研究。透過作者深入考察,認為范甯的立場並非僅是親《左氏》、敵《公羊》而已,對於公羊家向來採取不同立場的穀梁家,范甯雖然批判了《穀梁》先師不能“善於經”的立場,用作者的論點來說,即范甯雖意圖重建一個有體系的“穀梁學”,卻仍須援引鄭玄說與杜預注,援引他傳立己說;透過作者詳細論證,范甯在許多經傳釋義上,仍與彼所批判的先師一樣,採擇《公羊》與何注、《左傳》與杜注,俾以自圓通說之理。此點論述,不啻是使我們對范甯《序》中所言“據理以通經”“經以必當惟理”,有了不同的體會;同時也對范甯序所自言“集解”之義,有了更多的認知,非僅於書會共講輩而已。范甯《序》中多用“三傳”辭,如云:“《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又曰:“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蓋其序稱“《春秋》三傳”,此正緣於劉歆、班固、鄭玄以來之歷史脈絡背景。不僅此也,鄭玄的“三善說”也在范甯筆下繼承,范《序》云:“《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東晉時的范甯,顯然繼承了鄭玄的“三善說”,並帶出新的修辭論述,成為三家長短得失論。故本書中面對范甯之態度,實可自經學史立場入,非僅《穀梁》學醇度的體系化立場,則《春秋》學史上的鄭玄《春秋》學,亦適可見兼採今、古。若作者自此發論,言鄭玄綰合《左氏》、《穀梁》傳義,並影響了范甯面對二傳的態度,或不失為一有意義的探討。蓋唐劉知幾《史通》外篇云: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之初,專用《公羊》;宣皇以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譏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用朋黨,哤聒紛競,是非莫分。
蓋子玄雖宗《左氏》,然其云“三傳”紛競,自必同疇《春秋》方可。
作為歷史,范甯兼採《左氏》與《公羊》及親《左》敵《公》的例子,與本書上編作為末章的晚清柯劭忞《春秋穀梁傳注》類似。晚清民初之時,面對異文化東來之西潮,而有康有為與廖平對《公羊春秋》進行歷史激盪下之經學新建與古今再融;同樣的,柯劭忞的《穀梁注》也可以置於此歷史視域背景,進行《穀梁》柯氏學的探討。《穀梁注》中,柯劭忞著實提出不少新說,尤其是他將“內諸夏而外夷狄”進行“穀梁化”以用於內、外辭,正透顯柯劭忞對《穀梁》的解經重詮,有面對傳統之當代化意圖。柯劭忞的《穀梁》學,誠如作者所言,甚值治《春秋》學者關注,雖然近世學者頗未留意。許君之書則矚目柯劭忞,不僅對柯劭忞“古九旨說”進行分析,且留心彼書中所提出之“三臨之言”與“君子”論義,以為二說實與柯序中“古九旨說”共同構成《穀梁補注》一書大體,並為柯氏《穀梁》學核心。許君書中專論柯氏學不可謂不深入,甚至堪稱近代對柯氏《穀梁》學的一次重要“再發現”;揆諸梁啟超、錢穆兩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的對《穀梁》的闕頁,晚近以來猶是,則許君對柯氏《穀梁》學的探討,可在近代學術史留一位置,其並將柯氏學作為清代《穀梁》學史之殿軍篇章,亦深刻矣。
由鄭玄所提出的“《穀梁》善於經”,此五字不僅為許君大作書名,同時是貫穿全書的主軸與要旨。不論是上編的《穀梁》學史,還是下編的《穀梁》釋經體系建構的發論抉微,許君所關切者,皆始終環繞此五字:“《穀梁》善於經”。蓋有此主意主軸,方有清代諸儒對六朝范甯《穀梁》學之檢論,以及許君對清代諸儒著作再分析與再深究。蓋《穀梁》所以釋經與如何釋經,歷經清代諸家之努力建構後,究竟阮元、許桂林、鍾文烝、柳興恩,乃至於柯劭忞,他們的努力與貢獻對《穀梁》學與《春秋》學而言,是否已然達到了這一作為書名的層次與名實呢?顯然這樣的思考也存於本書作者心念。於是,由宣帝之《穀梁》中興與劉向學《穀梁》,迄於范甯之集解、楊士勛之疏,乃至有清一代諸儒,《穀梁》是否通達經義,自成《穀梁》一家言,這一層的思考,乃是《穀梁》傳史中必須面對《春秋》者,亦是《穀梁傳》所以存在之本;此議題自鄭玄提出“《穀梁》善於經”後,迄於今日,依據許君大作所析論,確然仍是一個可續之核心議題。
本書下編之三章,皆為《穀梁》大義發論之作,造詣深湛,甚達宏旨。蓋此三章乃分別就《春秋》之文本開端、中間與結尾而《穀》義新銓。開端與結尾各言《春秋》始乎隱元、終于哀十四,中間敘事則論齊桓、晉文事,言何以為“伯”義;孟子雖言《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然究竟齊晉何以有此權而行此事?此問則有“霸”與“伯”二義,兩解不同,褒貶亦異;《穀梁》主後者,故稱齊、晉為伯,為伯則周尊,周尊則道尊;齊桓有九合諸侯會盟之功,然在尊周視野下,《穀梁》發傳文仍持貶義,蓋齊桓、晉文行事合法性,來源仍在天子之所賦。作者嘗試在本章詮釋《穀梁》成家的立言道途上,引進柯劭忞的“三臨”之言以為詮釋《穀梁》體系的嘗試,不啻是拋出了一個近世《穀梁》學的議題,值得當代學界關注。
古今三傳家皆必面對《春秋》何以“始”與何以“終”,亦即“隱公”與“獲麟”問題。本書並未缺席。《春秋》首條自隱元年始,則何以始乎隱,正爲《春秋》學研究之大課題。對本書作者而言,《穀梁》所釋的隱元年義,便在於隱桓之際的正與不正,蓋此乃“《春秋》開端賦義,亦是其建構的《春秋》世界之源起”。《穀梁》之隱元解讀,特別是“即位”之不言,當自追索經文“正隱”爲的。如其所述,《春秋》“隱公”與“元年春王正月”,此八字雖簡,卻是作為首條而構成《春秋》開篇。歷來治《春秋穀梁傳》者既少,故專論《穀梁》義下的《春秋》“何以始乎隱”、何以書“元年春王正月”者更少。清初明儒顧炎武《日知錄》中撰有《隱十年無正》條,專門針對《穀梁》“治隱而正隱”而發,其謂“隱十年無正者,以無其月之事而不書,非有意削之也。《穀梁》以為隱不自正者,鑿矣。”吾人皆知顧氏主《左傳》而評杜注,尤其批判《公》《穀》之時間例,以為此乃國史書法,非是夫子削文;隱十年不書月乃是國史闕文。許君遵傳文“謹始”與“無事”義入手,則不啻與顧氏進行了一場傳釋對話,抉“正隱以治隱”義;蓋《穀梁》於隱公,實持貶義,其立場尤與《公羊》家以隱公為賢持褒相異;《公》《穀》傳文皆云“成公意也”“成公志也”,然一旦進入何以成隱公之志、意層剖析時,兩家在褒、貶持論上完全顯出殊異。《穀梁》之貶,建立在成隱之志上,惟“成公志”方能作為經文貶隱之“不言即位”之底蘊;是故必彰“隱讓桓”意,方能解釋何以“讓桓”為非是,並進至褒貶層次,言其“貶”義。正隱與治隱,此義自元年春正月至隱公十一年冬十一月壬辰,實貫穿隱公全篇終始,故曰“謹始”,故曰“終隱之篇”,皆貶隱公也;蓋《穀梁》貶義甚深故辭亦切,云“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云“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又傳文非僅於首條發義而已,於卷二末條經文“隱公十一年薨”,猶發傳云“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許君抉發《穀梁》正隱治隱之義,實甚深微,我們透過其闡釋,清晰理解《春秋》首條隱公元年不言即位大義,也大與《公羊》傳認可其賢義異。
其下編終章所討論者,為《春秋》之終,言問《春秋》末條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一部《春秋》,終乎獲麟,終于麟;“麟”之一字,其位置所居,實為整部《春秋》之末,則其義實大矣。一如《春秋》之末,仍為治《春秋》者所必面對議題,則《穀梁》傳如何發傳,如何闡釋此絕筆之義,則必本書當面對。許君以為,傳文對於“西狩獲麟”的解讀,其所面向者乃“中國”而非“魯”。《穀梁》發傳“大獲麟”“大其適”“不外麟於中國”“不使麟不恆於中國”義,作者於此自設問云:《穀梁》提出“大獲麟”三字,究竟乃“大”“獲麟”事,抑或“大”“麟”此物?蓋“大問”也。許君深道其底蘊,以“大其適”為據,解所大者為“麟”,故“麟之來”而不言“來”,“不言有”則麟恆常居中國,故曰“不外麟於中國”,又曰“不使麟不恒於中國”,傳文兩言中國,則中國孰解?作者此處引入范甯之注:“中國者,蓋禮義之鄉、聖賢之宅,軌儀表於遐荒,道風扇於不朽。”深刻挖掘了文化性上的“麟與中國”在《春秋》文本上關聯的重大意含。
本書既論“麟”之主體常在恆有而為著作終篇,亦符於《春秋》之末以“麟”字絕筆。全書九篇章,上編詮釋之史,下編始隱、終麟。但凡寫作,如道途行遠,必歷艱辛,乃見登高之豁。學術世界立言之事,則俟後世,惟恐名山見棄,君子所哂;此所以憑案而書,擱筆至要。予讀許君行文,往往重重思又重重斟酌,所以故為何?蓋所書世界將停墨也,筆墨凝時,即篇終之日。書寫之責在己而文本在世,故君子所懼,末辭末字,忖之再三,故有終篇之義,以殿全書。
許君此書積累經年,以博士論文為基礎,曩昔曾至華師參與其博士論文畢業答辯,故甚稔其成書歲月。許君此書專宗《穀梁》,傳學《春秋》,故以“《穀梁》善於經”為題,貫穿全書者盡在此五字,旨趣皎然;謂此書將必為治《穀梁》者所重,符名實也。予則尤愛此書緒論與鄭玄、楊士勛、學海堂諸儒、柯劭忞等《穀梁》學諸篇;下編始末正隱、論麟、言伯三章深義再銓,尤其專門《穀梁》者之言。
予之與超傑博士相識,始於予至滬上華東師範大學思勉高等研究院客座,授課史學,許君則為博士生,亦來聽課,課後問學,情懷頗契。逾年,許君已申請獎學金並來函云欲赴台我處共學,蓋予於研究所開設《春秋》與《史記》課程也。敝學校在山海之間,許君則於礁溪賃房而居,整一學期間惟學而已,惟《春秋穀梁注疏》與清儒《穀梁》學而已;閑時或海邊、洋畔、山徑,或書、或茶,或自蘭陽往返台北國圖、中研院傅圖、文哲所。許君與予或聚於其所居處,或於予之研究室,每每砌茶啜品間,多有談笑問學白雲僻巷居築歲月可共,迄今猶能憶之。後予至曲阜孔子研究院任職,寒暑間帶領曲阜諸君子共讀《春秋》與三傳,許君亦來相伴,商量課程與會議;曲阜入冬頗雪,予猶憶某次大雪,予偕許君共往孔林游,道途徑中古木參天,白靄吹雪紛飛,倆人步往子貢築廬夫子墓旁故處舊址,徜徉良久;許君之論“麟”篇章,即在此時完成也。許君獲博士後,受聘湘湖岳麓授學上庠,睿思沉潛,多年後學術造詣,又非昔日書卷等第,而更望江樓之遠矣。今許君大作即將問世,付梓在即,予因述其學與此書閱記,並許君之性情懷抱與讀書樂學之情,宋明儒所謂孔顏樂處者,許君蓋其世界中人歟!於是乃述其學,道其人,並誌予憶。是為序。
李紀祥
歲次癸卯冬,2023年12月26日於台北寓所
後記
聖如日月,普天皆有春秋;道若江河,隨地可成洙泗。
——嶽麓書院大成門對聯
自漢武帝推崇經學儒術以降,孔子作為儒家的開山祖師、六經的正定者,從生前鬱鬱不得志的儒者變成了後世仰望的聖人,如日月一般普照大地。所以然者,古人認為孔子所正定的六經,寔為後世“制法”,雖千萬祀亦當遵之、準之。孔子修六經,但真正由其所作者,亦不過《春秋》而已。是以,“普天皆有春秋”,亦普天之下皆當遵從《春秋》。江河流轉不居,所到之處皆受其惠;即如孔子之道,二千年來皆受其濡潤。
但孔子畢竟已經逝去二千多年,孔子之道也已被人棄之如敝履,似乎離我們越來越遠了。2016年4月,我第一次來到曲阜,這塊曾經哺育聖人的土地。從酒店坐車到孔林,只用了十分鐘;從孔林走回酒店,用了整整半天。不是因爲路途遙遠,而是由於這塊曾經的聖地、聖域,給了我太多的衝擊。花了很長一段時間讓自己平靜下來,在午夜的曲阜,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孔林儼然已是文化旅遊之熱點,無論是巍峨的牌樓前,抑或通往夫子墓的洙水橋,都人頭攢動,好不熱鬧。然熱鬧只屬於表面,吾人只需沿著步道走出二三百米,除了周遭一壟壟墳丘和墳前或巍峨、或殘敗的墓碑,卻只有我一人獨自走過了。當我走過三分之一時,心中好不慘然。墳丘中埋葬了當年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或耀眼、或黯然;墓碑用短短一二行字書寫下墓主的生命與履跡,或顯赫、或慘淡。但耀眼也罷,顯赫也好,終歸成爲一壟墳丘、一塊石碑,所不同的,不過是墓前多了、少了兩頭溫順的石獅、石羊。唉,人生輝煌,終歸敵不過這時光流逝、日月不居。
天地蒼茫,時光無限,人實在是太過渺小。看著墓旁樹木的奇姿百態,不禁羨慕樹木之壽。雖然默默淡淡,卻自我獨立,不必等待身後的書寫。反倒是人,雖或轟轟烈烈,終歸是免不了留待後人“蓋棺定論”,定義這個“人”之爲“人”。
還好,終於見到了孔林深處的一束鮮花,斯人雖逝,卻亦不曾完全逝去,其生命已爲後人所承繼,其精魂仍爲後人所惦念。人生幻滅與永恆之間,終究還是不絕若線的。夫子也是一樣,夫子的幻滅與永恆之間的轉換,終歸不在肉身的存與亡,而在夫子精神的永恆與否。當衍聖公墓前的石獅子被磨成光滑圓潤的時候,當神道旁只有溫順、屈膝的石羊時,衍聖公已不過是夫子生命之延續,而不再是夫子精神的承載了。
余英時先生說:“我在哪裏,哪裏就是中國。”曾爲聖域的孔林,倒也符合余先生的這句話。當諸弟子守喪、子貢廬墓之時,當眾人重拾夫子言行、編撰《論語》之時,孔林當然是夫子的聖域。但當孔林只是一碑“嚴禁煙火”、一車車從下馬石前馳過的遊客時,就已不再是“聖域”了。夫子的聖域,實在其所述所作的《春秋》中,在諸弟子結構的《論語》中,在華夏文化的傳承中,但並不獨在這片土地中。
當夫子以“西狩獲麟”爲《春秋》寫下最後一筆之時,怹早已爲我們結構了怹認可的、建構的“聖域”;當穀梁子以“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解讀“西狩獲麟”之時,怹早已爲華夏文化創立了一條進入夫子“聖域”的神道。只是千餘年來,吾人總在遙想遠方的“聖域故事”,卻不曾注意腳下的“聖域之路”。夫子與後學結構的《春秋》《論語》《詩經》《尚書》《儀禮》《禮記》《周禮》《周易》在在都是通往夫子“聖域”的“通途”。“優入聖域”四字是古今儒者的大追求,然“聖域”在哪?不在一時一地、不在從師與否,而在於詩書禮義之間,在夫子精神世界之中。
千年之後,當我懷著朝聖的心情踏上久遠的“聖域”,但“聖域”所帶給我的,卻是對“聖域”的祛魅。還好,當有形的“聖域”悄然崩塌的同時,我也找到了屬於我的“聖域”。原來怹一直在這裏,在千年傳承的儒學榮光之下,在洙泗洛閩的道脈之內。孔子曾感歎:“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既未之逮,如何“有志”、如何賡續呢?蓋“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是所以孔子雖不及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卻能有志以賡續。孔子雖已逝去二千多年,但正因為有其正定的六經,讓我們在千年之後仍能賡續其道。是以,只要能夠透過六經以追尋孔子的精神,我們仍能接續孔子之道;只要能夠研讀六經,亦“隨地可成洙泗”。以我的淺學無識,當然不敢說接續了千年的儒脈道傳,只是感到很幸運,機緣巧合,能夠選擇《穀梁》作爲志業,在當下的現實世界中,用《穀梁》回望夫子之“春秋”,讓我有機會重新審視《穀梁》“不外麟於中國”又“不使麟不恒於中國”的聖人書寫與聖人之道,使我有機會探尋“聖域”所在。
“優入聖域”這四個字大概是古代學人的終極理想,但對當下的學者而言,卻似乎已經是陳年舊事,不過只是一闕牌樓罷了。說實話,從本科到碩士,雖然也讀了一點點經學儒學著作,但都是“祛魅”之後的閱讀,而不能真正體會古人對於“聖域”“經典”的尊崇、優思與想象。真正讓我親近經典、走近“聖域”的,大概就是李紀祥教授。2014年春,李老師客座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思勉高等研究院,開設《明清輿圖史與世界觀專題》研究生課、《史通》讀書會。機緣巧合看到李老師課程海報,即去旁聽。在聽了李老師第一堂課之後,我就堅定地說,我喜歡、欣賞、崇拜這位老師。此後,從櫻桃河畔到宜蘭礁溪,從聖域曲阜到麗娃河邊,亦步亦趨,跟隨李老師的步伐,希望能夠走近“聖域”、走進“經典”。
要不是因為李老師,我根本不會想到選擇《穀梁》作為日後研習的課題。李老師認為學者應該有其根本,專研一經是為建立根本之最佳途徑。《穀梁》歷來研習者少,不妨以此入手。2015年秋,赴佛光大學跟從李老師學習一個學期,老師每星期都會有半天專門批改論文,與我談《春秋》與《穀梁》治法。本書下編論《穀梁》義下的“《春秋》始隱”說、“齊桓晉文之事”和“西狩獲麟”初稿,都是在礁溪林美山李老師耳提面命之下寫就的。細細婆娑李老師批改的厚厚一疊論文,靜靜閱讀那“五彩斑斕”的批校本,深知如果我真能一步步接近“聖域”、一點點漸知“經典”,這一步一釐的前進,都是李老師在背後默默推行。2016年暑假,陪侍李老師在曲阜講學,當最後一講結束時,我在課上說過:
當兩千多年前,孔子就在這裏,就在沂河邊上,跟弟子講“賢哉,回也”,這才有了“顏淵之樂”;在兩千多年之後,又在這沂河邊上,在這個教室裏,李老師帶我們讀這一章的時候,我們也在尋找“孔顏樂處”。我覺得兩千多年的時間間隔,就在這個地方交匯了。從李老師身上,我知道了什麼叫作師道尊嚴,什麼叫傳道受業解惑也,什麼是孔門的傳承。
不敢自比孔門弟子,但李老師正在做、也是一直在做的,都是接續孔門學脈,這是毫無疑問的。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願在李老師的指引下,最終能夠走近“聖域”、走進“經典”吧。
當然,還得感謝我的博導戴揚本教授,要是沒有戴老師的寬容,容我隨意妄爲,選擇《穀梁》這樣一個很“守舊”又不太可能出彩的課題作為博士論文,也就沒有日後的《穀梁》學研習。事實上,戴老師對我的治學態度、人生態度和對西學與理論產生了極為重要的重視。就我的性格而言,伉急狷介,又敏感焦慮,有失平和之氣。猶記得臨近畢業,跟老師在秋實閣吃飯、對酌之後,當著老師的面大哭過一場。如果沒有戴老師的開導與指引,或許難免太過偏執,難免偏離人生與學業的“主線”。
而就西學與理論的學習而言,則在畢業之後才真正體會到老師的用意。老師在序中說:“所謂‘歷史感’,不止是歷史背景知識的敘述,更重要的是一種自覺的思維方式,就像研究社會須從最初的社會經濟關係出發一樣,研究思想應該是研究感性活動的主體即人的種種社會活動入手。”這是老師對我這篇文章內在思路的一種提煉,但這種思路的形成正是在老師的指引下產生、成型的。
我始終覺得,人文學科最終不過是在書寫一個“人”字。研習經典,更重要的就是要去體會文本背後的那個“人”。戴老師不但博學,更爲博識,將所學之“知”與所歷之“識”完美的結合起來,成就了一個大寫的“人”。從戴老師身上,不但學到了如何作學問,更明白了當如何作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一個人格完善的“人”。老師所指引我的,不但是如何為學,更是如何學為人師。
正是在李老師的推動和戴老師的寬容下,我最終選擇以《穀梁》學為研究對象,又結合“十到十九世紀思想史”的博士研究方向,確定了《清代〈穀梁〉學文獻四種研究》這一博士論文題目。2017年6月畢業、工作之後,日漸覺得若就單章而言或不無可取之處,但就全文而論卻實不能讓人滿意,至少不能讓我自己滿意。故發心以“《穀梁》善於經”為中心,重論《穀梁》學史與《穀梁》學體系,是以有了這本小書。
從2015年確定以《穀梁》為題、2017年寫完博士論文,即使是從2019年獲得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立項以來,也已過去多年。多年耕耘,不過寫就了這樣一本小書,實在有些讓人汗顏。或許聊可以為藉口的,就是結婚生女,每天要面對柴米油鹽醬醋茶,學術只能讓位於生活吧。但就像前文說的,人文研究的核心不過就在一個“人”字上,要去探求文本背後的“人”,更要讓學術回歸到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中去。正是因為與我愛人相知相愛相守,才讓我更能明白生活的意義與包容的可貴;正是女兒的到來,讓我更體會了這個世界的無限可能與愛的真諦。
也許正是有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瑣碎細節,有喜怒哀樂的轉換,才能顯出這是一個真實的世界。沒有必要神聖化學術研究,讓人文學術重新回到活生生的生活世界,這樣的研究才有意義,這樣的學術人生也才更為真實。其實古往今來的大學者哪一位不是在這樣的瑣屑生活中成長起來的呢?哪位真正學者又沒有自己的困厄與無奈呢?學術本就應該從生活中來,也應該回歸到生活中去。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一切歷史都應該是活生生的歷史。無論孔子還是穀梁子,抑或是范甯、楊士勛、柯劭忞,都是在書寫歷史、接續歷史、創造歷史,從歷史中來、到生活中去。要真正接續《春秋》學、《穀梁》學傳統,大概仍當回到歷史與生活中去吧。
余英時先生說:“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錢,就能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別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畫虎不成反類犬。總而言之,盡力完成自我,同時也知道尊重別人,這是所謂‘博學知服’,即是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的最好辦法。”自知沒有多少本錢,做不了大生意,但至少要努力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
是為記。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汉语研究与社会应用实验室
文章原创|版权所有|转发请注出处



